回忆作家陈国凯——黄纯斌
2019-09-24

◀著名作家陈国凯曾担任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18年,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、广东省文艺终身成就奖获得者。 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片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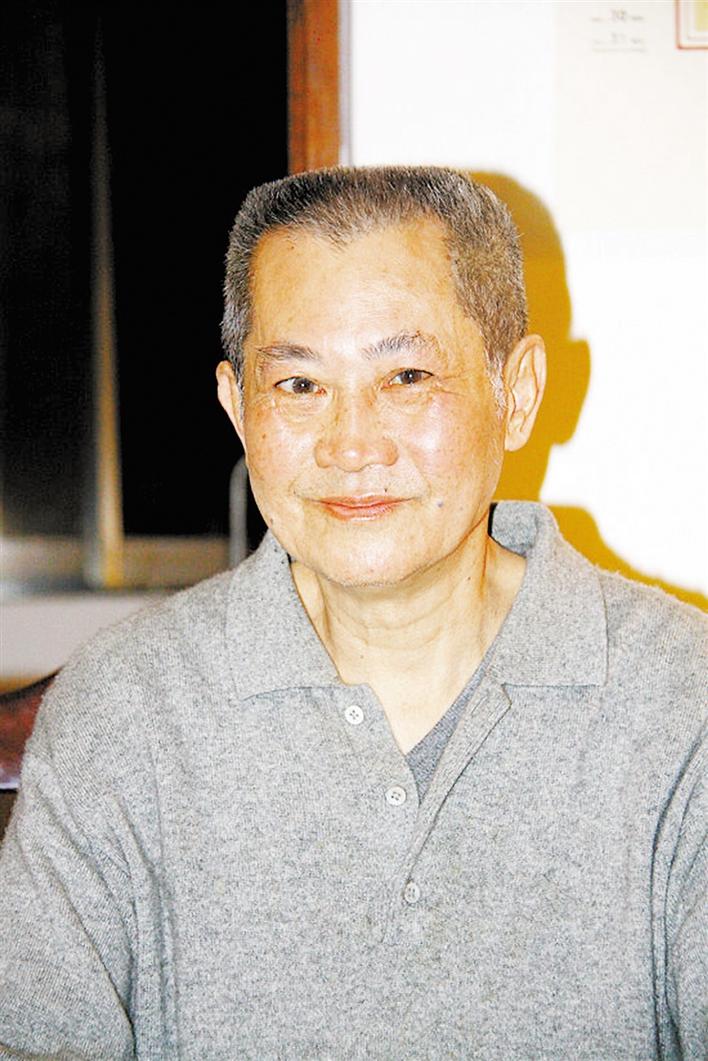
▲晚年陈国凯。
◎黄纯斌
陈国凯是我非常尊敬的著名作家。他于2014年5月病逝。因信息不及时,我没有参加他的追悼会,这成为我久久的遗憾。

陈国凯长篇小说《大风起兮》讲述特区创业史。
《一方水土》取材蛇口
“文革”结束不久,国凯发表了小说《我应该怎么办》,誉饮文坛,成为“伤痕文学”的代表之一。自此我知道了国凯这个名字。以后听说他是梅州五华客家人,就更加关注他的信息了。
1983年,我在梅州《梅江报》编辑部工作,被临时抽调到地区人口普查办编简报。一次因公出差去广州,到兴宁军用机场坐民航班机。进入小小的候机室,看到一位眉清目秀的中年男子弓着身子横躺在靠椅上,睡得很香,很雅静,没有人去打扰他。登机时,他起身排队,我一眼认出他就是国凯,因为我在一个公众活动上见过他,只是没有交流。我想走上前去自报家门打招呼,又怕唐突,且自己手里又提着沉重的行李,便放弃了念头。
1990年,我已供职在深圳南山区委办公室两年。深圳特区文化研究中心的同乡杨宏海,邀我到通心岭国凯家里拜访,祝贺他当选广东省作协主席。这是我第一次与国凯交流。他长得斯文、瘦弱,高度近视眼镜后面的两只眼睛炯炯有神,会把人看透似的。他用客家话与我们交谈,讲话不多,慢条斯理,很亲切。
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南山区,是深圳的“郊区”,离市区20公里的沙石公路,弯弯曲曲,高低不平。辖区有特区开发最早的蛇口和最偏僻的西丽。区里主要领导都是知识分子出身,注重对外交流。我几次邀请国凯,他都高兴地来了,还带上夫人纵姨。他没有大作家的架子,礼貌、随和。我们一起聊区里的情况,聊闲情轶事,聊客家风情,似有聊不完的话题。他曾在蛇口体验过生活,对蛇口不陌生,其长篇小说《一方水土》中的不少素材正是取之于此。
唯一头衔是“中国作家”
深圳特区开发建设初期,中国作协独具慧眼,捷足先登,选在风景秀丽的西丽麒麟山下建了创作之家。这里,背山面水,鸟语花香,夜晚萤火点点,蛙声一片,如世外桃源,是激发灵感之地。中国作协常组织知名作家到此疗养创作,也让他们感受特区建设的氛围。
一次,高晓声来了,国凯安排接待,叫我作陪。
我看过高晓声的作品,其《陈奂生上城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。与二位知名作家在一起,我有点兴奋。高晓声其貌不扬,一副苦大仇深的农民形象,与其幽默的作品很难联系在一起。两位作家的普通话都不标准,国凯是带广府味的客家普通话,高晓声是南通口音很重的普通话,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交流,他们谈得很投入。两人都有农村经历,高晓声成功塑造了陈奂生的农民形象,国凯成功塑造了阿通农民和工人的复合形象,他们在一起,难免会有共同话题。
高晓声对特区很感兴趣,想到农村去看看。国凯让我安排并陪同。当时的南山,还是特区中的“农村”,我向领导请示后,安排高晓声到南园村走访。村里的吴书记见过世面,介绍得有条有理,只是其当地普通话高晓声听不懂,高晓声的话他也听不懂。我从中作翻译。高晓声很认真作笔记。他的钢笔书法很漂亮,有江浙姑娘的秀丽感。至于这次采访有无成为他以后创作的素材,我不知晓。
国凯身为省作协主席,而居住在深圳,工作有所不便。他说他践行无为而治,抓大放小。他这个主席似乎当得轻车熟路,游刃有余。他深居简出,不把过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应酬上。外省市重要的客人和朋友来了,他也不失礼节,尽地主之谊接待。我陪他接待过蒋子龙、邓友梅、徐迟、赵本夫等一批知名作家。有些作家还成了我的好朋友。
国凯为人低调,不事张扬,不务虚名。他给过我一张名片,唯一的头衔就是“中国作家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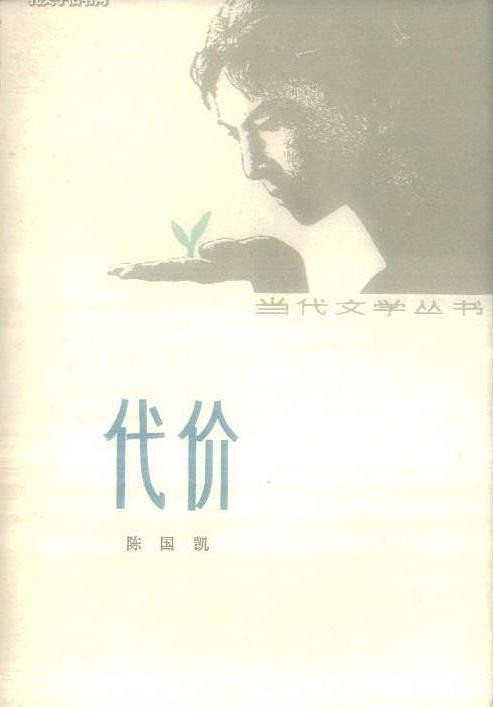
陈国凯长篇小说《代价》。
他是骨灰级音乐发烧友
国凯是性情中人。他曾经多次和我聊过人生,聊过家庭,他有一种特殊的视角。这,与他的经历有密切的关系。
国凯出生于1938年,祖父旧时是大律师,曾当过苏州法院院长,家里藏书丰富。他从小受文化的熏陶,打下了良好的古文功底。在阶级斗争年代,这种背景让他吃尽了苦头。爱情的女神偏爱这位才子。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,当时有傲人条件的大学生纵姨投进了他这位普通工人的怀抱,结为伉俪。他们几经风雨,恩爱有加,情深意笃。国凯称她“有妻子的纯真、母爱的温柔,还有严师般的教益”。国凯长期带病创作,为了支持他的事业,纵姨既当保姆,又当文秘,包揽家政,毫无怨言。谈起妻子,国凯总会露出自豪的笑容。
有一次我到国凯家拜访。因彼此熟了,未事先预约。叫开门后,客厅里的场景弄得我莫名其妙。一张大大的棉毯吊在墙壁上,国凯半躺在懒人椅中,静静地欣赏音乐。他解释了一番,我才知道棉毯是用来听音乐的。
国凯领我浏览新改造的书房,书架上放着一排排CD唱碟:古典的,现代的;钢琴的,小提琴的;贝多芬、肖邦、莫扎特、柴可夫斯基等等,等等,分门别类,比音像店摆放得还整齐。客厅是他的音乐厅。他说客厅装了28个大小喇叭,主线一米就花了一二千元。他当过电工,音响组合从选材到安装都是自己完成的。闲暇时,他喜欢躺在椅子上欣赏音乐。他说音乐中有尽善尽美的环境,人的思想最为自由,灵感可以发挥到极致。
国凯发表过《发烧友手记》专著,令音响爱好者叫绝。其把文学的元素,有机地结合到音响专业知识之中,使枯燥的音响知识艺术化。
国凯善于在生活中发现创作素材,善于在音乐中获取创作灵感,这应该是他的文学创作有取之不尽的源泉之奥秘。他逝世了,中国文坛失去了一位优秀的作家。去到天国,也许他也闲不住,他的作品《我应该怎么办》提出的问题不是还没有解决吗?他还要去寻找艺术的答案。

 粤公网安备44030002006750号
粤公网安备44030002006750号


